
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2007年,这一年苹果发布了它坊间传闻已经的产品iPhone,从而宣告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在第一代iPhone发布会的第4分57秒,乔布斯开始向与会者具体介绍这部手机,进入现场观众的第一个Keynote标题,不是处理器,不是App Store,而是“Revolutionary UI”——革命性的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
实际上,”用户界面“,也是在整场发布会中少有的,乔布斯在同一个细节演示了两次的特性。他通过手指滑动解锁了手机,全场鼓掌,观众显然没见过这个,于是乔布斯显然被鼓舞了,于是问,“你们想再看一遍么?”,然后他立刻再做了一次解锁。
01
用户界面:机器灵魂
“用户界面”看似简单,但是它值得乔布斯用这么重的笔墨去呈现,因为“用户界面UI”的历史,就等同于个人计算设备的发展史。
最早的计算机雏形,可以追溯到距今200年前。1820年,英国数学家、发明家兼机械工程师,提出了计算机的设计概念。不过从1940年开始,计算机被真正发明的前30年里,计算机都和个人无关,它只是专业的科学运算装备。直到1971年,售价750美元的Kenbak-1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第一次刊登广告,又一个10年后,全面引导个人计算普及的IBM PC出现,计算机才开始成为一种“个人设备”。
自IBM PC面世,已斗转星移40年,个人计算设备的销售数量也以数十亿计算,个人电脑成了智能手机,固定拨号上网变成移动互联网。变化不可谓不大,但是如果从用户界面的角度看,个人计算设备只历经三代体系更新。
1981年开始的IBM的个人电脑时代,用户界面是以键盘敲击为核心的命令行。在1992年、1995年,微软先后发布Windows 3.1和Windows 95后,以鼠标移动为核心的视窗,成为计算机的主流界面。然后才是2007年,我们开篇提到的乔布斯故事,iPhone宣告了以手指滑动为基础的触控界面。
回顾40年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巧合的15年周期规律,每隔15年左右,用户界面体系才会规律性的进化。而随用户界面而变化的,则是设备形态的全方位变化,软件升级,硬件换代,市场格局剧变。用我采访的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成录博士的话来说,操作系统是设备的灵魂,用户界面就是操作系统的灵魂。
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不难理解,个人计算设备,之所以可称为“个人”设备,主要是因为它作为机器,具备和“个人”进行交流的方式,这个交流方式就是操作系统的“用户界面”。交流过程是否顺畅,易懂,则决定了“人”是否有意愿使用“机器”。而机器底层的操作系统也好,硬件配置也好,其实某种程度,都是为最上层的交流方式——“用户界面“服务的。因为用户界面是用户除了机器的样子这个外表因素之外,对机器唯一能直接感知的东西。
现在,2020年伊始之际,从2007年到现在,又一个15年周期临近了,用户界面又将向何处去?
02
历史故事:封闭与开放
预测未来,有两个常见的说法。第一句话是,我们大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关于未来的答案。第二句话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你可能无数次在不同场合听过这句话。绝大多数时候讲这句话的人,只是一个灌输心灵鸡汤的演讲大师。但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却是这句话不折不扣的行动贯彻者,他就是天才计算机大师,也是图灵奖获得者阿伦·凯。
阿伦·凯有多传奇,我们用一小段故事来讲述一下,毕竟他的创造和我们今天要讲的用户界面息息相关。阿伦·凯是超智商儿童,就是你知道的三岁能看书,五岁上小学就读了几百本书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对儿童很感兴趣,1972年,阿伦在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工作,他尝试用他发明的 Smalltalk语言应用在儿童教育上。
于是,研究中心来了很多孩子,他让他们学习使用电脑,并记录儿童的使用的过程。阿伦在研究了这些素材之后认为,和操作文字相比,多媒体图像、声音可以让儿童更方便的操作电脑,“视听元素”是用户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于是,他开始研究图形化界面,并发展出研究成果。
到1979年,乔布斯和其他几个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到施乐帕洛阿尔托中心参观时,乔布斯发现了阿伦·凯的图形界面原型,他感慨“Smalltalk语言灵活、易用,简直就像是为苹果机量身定做”,并坚定了走图形化界面的道路。因此,无论是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Linux窗口,还是苹果电脑,之后一切图形化的操作界面,都可以认为是阿伦·凯划时代构想的继承者[注1]。也正因如此,当乔布斯批评盖茨领导开发的WINDOWS抄袭了苹果电脑的图形界面时,后者只要微微一笑,“你不也是从施乐看来的么”。
但今天我们还要引用阿伦·凯的第二句话,“真正认真写软件的人应该自己做硬件”(People who're serious about software should make their own hardware.),这句话就被乔布斯2007 年第一代 iPhone 的发布会上了。阿伦·凯的原意是,优秀的科技公司应该精通“软硬件”两个知识体系。不过乔布斯更想以此证明,只有苹果软硬一体的集成体系才能做好个人设备。
计算机发展史始终存在两种流派,一种是封闭的,自己做所有事,一种是开放的,和生态伙伴一起经营平台。而苹果的Mac电脑是封闭的,它从硬件基础平台一直做到操作系统用户界面,而微软的DOS/ WINDOWS体系则是相对开放的,英特尔、微软、应用开发商、PC厂商各司其职。当然,基于开源技术的Linux平台则更为开放。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起码在PC时代,开放平台战胜了封闭平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苹果总是先创造出一些新东西,但是PC阵营总能后来居上。在智能手机时代,作为先行者的乔布斯显然希望扳回一城,想证明起码在这个领域,封闭集成体系比开放架构更好,他的iPhone也确实完成了封闭体系的大一统,从App分发“App Store”,到操作系统iOS,再到芯片硬件,是完全一体化的,没有一样是开源和开放架构(其实,在操作系统最底层苹果也用了开源技术FreeBSD)。
所以乔布斯的这句引用,可以看作是对苹果在PC时代,败给微软DOS/ WINDOWS体系的耿耿于怀。不过历史却又一次重演了。封闭的体系固然简单可控,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却意味选择的减少。在任何市场,消费者的需求都是多样的,参差多态方是幸福本源。于是在谷歌的安卓体系出现之后,智能手机市场几乎重演了微软DOS/ WINDOWS一幕。
从结果来看,尽管苹果依然控制着这个市场的大部分利润,但是如果以市场占有率计算,安卓体系又像当年微软DOS/ WINDOWS那样占了上峰。
但这个开放和封闭之间的追赶过程,并不简单。
0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小李飞刀,名震江湖,靠的就是一个快字。对手没看见李寻欢出手,飞刀已经近在咫尺。对于用户界面来说,运行速度也是非常直观的参数。
但安卓的天生难题就是——不够快。在具体关乎消费者体验的用户界面方面,安卓体系不完美。和相对流畅的iOS用户界面相比,“卡顿”二字几乎贯穿安卓手机发展的始终。
这一方面是安卓的天生缺陷。在安卓4.4版本之前,谷歌在底层机制使用了Dalvik Java Virtual Machine,大家无需关注技术细节,总之相对iOS而言,安卓系统的虚拟机运行机制效率远远不及,它消耗了过多硬件资源。在安卓4.4版本之后,谷歌改进了底层机制,引入了ART 模式,优化了系统运行机制。但卡顿问题,并未在之后消失。似乎乔布斯2007年引用的阿伦·凯的话应验了,问题出现软件和硬件协调适配上。
王成录博士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深有体会,2014年,在华为手机用户界面平台EMUI (Emotion UI,华为手机的用户界面体系)4.0期间,他来到华为消费者软件部门。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王博士都是在和电信软件打交道,解决消费者软件需求,对他也是新课题。一时间,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必然相当多。
不过华为企业文化中有一个核心原则叫压强原则,也就是强调要将力量凝聚到一个点上做突破。《华为基本法》中有明确的表述:“华为坚持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在此哲学影响下,有个课题,很快摆上案头,成为重中之重,这就是刚才提到的直接关注消费者体验的速度问题——卡顿问题,“当时消费者对卡顿的吐槽量是极大的,我们想,在组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定要聚焦,反复筛选之后,华为手机要解决的第一核心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卡顿问题解决掉”,以达成解决之后EMUI 5.0发布时的口号:“天生快,一生快”,这也是华为用户界面进化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处理问题的思路,是笨办法,“我们直接研究消费者的问题手机“,“将消费者投诉严重卡顿的机器数据脱敏以后,用新手机换回来”,如果比喻为破案,这就是保护案发现场,华为当时收集了470多部手机。王成录对团队的要求是,“不要有任何主观去判断这样一些问题手机,要实事求是的还原现场”。
问题一:嘈杂的App开发机制
五个多月后,470多台机器全都复原,“分析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因为分析完这400多台机器,占在第一位的原因不是硬件本身,而是第三方App质量上的问题,它占了卡顿手机的21%之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安卓本身是开放的,所以每个应用开发者都基于自己的理解和知识背景来做开发,所以带来非常多的问题,比如应用之间互相抢占系统资源,导致内存泄露,从而让系统崩溃,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感受不到是App的问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华为应对的思路是联合腾讯、阿里、百度、网易等主流App开发厂商建立安卓绿色联盟,现改名为软件绿色联盟。
作用就是让中国安卓应用开发慢慢形成标准,避免软硬协调不匹配。华为在联盟中的工作,是免费提供设备给开发者,并把对安卓软件平台的理解贡献给业界,“自联盟成立,我们每年都做三四十场技术宣讲,包括告诉开发者如何适配代码接口,如何节省硬件资源调度等等”,最终在App开发者中间形成了标准和共识。现在,这个联盟已经不局限于补短板,而是有不少面向各种新场景的沟通工作。
“赛博故事”应约参加过一场该联盟活动,主题是面向折叠屏幕手机,如何开发App用户界面,这就是个创新问题。
问题二:复杂的硬件配件协同
原因之二则和硬件有关。和苹果集成化、统一化硬件规格不同,也是安卓手机厂商,尤其是中国安卓手机厂商初期供应链把控能力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卓平台手机的硬件配件标准也并不统一,小到内存,大到一块屏幕,往往是不同供应商。尽管在采购时,手机厂商有统一的标准要求,但是由于不同供应商天生能力不同,在参数细节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比如内存配件,都是128G的Flash,有的厂商能做到数据量使用到127G还有5M/秒的读写速度(作者注:5M/秒是一个关键指标,一旦内存传输速率低于这个数值,就会影响消费者体验),而另外一家厂商的Flash,可能还有十几G空间的时候,传输速率就跟不上了。问题也许会出现在NA内存颗粒上,更也许会出现内存的UFS控制器上。
找到问题根源,解决方案也就应运而生。华为用了大数据方法来处理问题,将供应商配件的屏幕驱动、Flash算法,甚至相机参数等全部归类,针对不同供应商,形成不同的参数调优模型,反过来告诉配件供应商,如何调整硬件参数,才能更好的适配,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
问题三:硬件资源调度的问题
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一台计算机。无论何种应用,跑游戏,播视频,或者写文档,都涉及到对底层计算资源、IO资源,内存资源等的消耗;但不同的应用,对于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有的需要大计算量,有的需要大内存空间,“给计算力需求大的应用,留内存空间就是没有价值的”,这就需要一个应用调度引擎,根据不同的应用类型,匹配不同的资源储备。具体到消费者应用场景,消费者在使用手机时,其实也有不同的优先级的,正在玩游戏的用户,一定不想后台的网页刷新影响游戏掉帧,从而让游戏角色出招不连贯。
王成录博士介绍,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不是单单追加内存就有效的,所以华为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做了一个围绕智能资源调度技术的系统调度引擎,能够感知应用特征,预先配置合适的系统资源,据王博士讲,“这个引擎非常有效,应用特征识别准确度从第一个版本的85%,进化到现在的 99.9%””,系统运行效率也就提高了。
这种自动调度的思路,延续到EMUI10版本,有了一个“确定时延引擎“的新称号,实现了更广泛,更准确,当然也是更智能的资源调度适配。
当然除此之外,面对“慢”的问题,以华为为例,还有诸多配套方案,如GPU Turbo、link Turbo、EROFS文件系统以及方舟编译器等,都是不同于安卓原生平台的技术方案。有意思的是,其实上述很多技术,华为并非是为智能手机专门开发,而是早就有的技术储备,然后被发现适用于现在的智能手机场景。
拿方舟编译器举例,这项技术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十年前,2009年,华为海思创建了编译组,4年后,华为发布了面向基站的编译器HCC,可看作是方舟编译器的前身,接下来2014年,方舟编译器主架构完成,再是2016年成立编译器与编程语言实验室,最终 2019年华为正式发布方舟编译器。
这个例子似乎能够说明,和操作系统、用户界面相关的问题,都是大系统,大工程,没有多年沉下心来的技术储备,很难取得成果。
04
人因工程:数学之美
“快”很重要,但是对用户界面而言,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外一面是“美”——“美而易用”。某种程度来说,这更重要,毕竟对于买手机等智能硬件而言,人人都是“外貌协会”,甚至黑客都不例外。
1991年9月17日,操作系统世界发生了一个大事件。一个由个人先行创造,接下来依赖社区贡献的开源操作系统上传到了服务器上,它就是芬兰人林纳斯(Linus Torvalds)主导开发的Linux操作系统。林纳斯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黑客或者极客,他用计算机,是可以不用“用户界面”的,直接上代码。他之所以开发Linux,就是觉得计算机上原来的操作系统性能不够好,所以自己写了一个。
不过即使这样的黑客,也需要美而易用的东西,这他自己都没想到。
1992年,Linux系统发布一年之后的春天,第一代X视窗系统开始在Linux系统上运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Linux系统能够支持图形用户界面。这个工作当然不是林纳斯本人做的,而是一名叫做的奥瑞斯特·扎布洛斯基的黑客搞出来的,它将X系统植入到了Linux平台之中。在最早期,林纳斯本人并不适应图形用户界面,毕竟他只用编程代码就可以操作电脑了,所以“我一时半会还适应不过来,有了这个功能的第一年里,我还很少使用它”,林纳斯在自传《只是为了好玩》中写道。
但很快,林纳斯发现了视窗界面的好处,并开始依赖这套更美观易用的用户界面,“但现在我工作时打开的界面数都数不清,要是没了这个功能,我简直就没法活了”,林纳斯后来感慨。所以,美是操作系统的重要要素,如果把用户界面画作一个太极图,其中阳代表效率的快,阴就应该是代表易用的美。
不过和快相比,美很抽象。我们说起美,经常想到天才灵感,美不像快,更有迹可循。乔布斯过世后,iPhone的用户界面由拟物风格,转向扁平化风格。当时批判声不断,认为乔布斯不在,苹果就失去了基本的审美判断力。你看,在大众习惯认知当中,和个人好恶关系甚密,而非判断为一种科学。
但其实美也是可解释的。
在影像构图当中,我们都知道拍照不能把人拍在画面的正中央,而是略偏于画面一侧。如果把整幅画面的宽度看作是1,那么将人物放在接近3/4刻度的位置,画面看起来更和谐。数学可以解释这件事,这就是最基本的0.618黄金分割原理。在西方世界,人类历史上最美的画作之一是《蒙娜丽莎》,而它的作者达芬奇同时是一个数学天才,美和数学密不可分。
因此,即使对数学家而言,美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哥白尼之所以不认同托勒密的天体运行体系,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竟然是——托勒密提出的偏心等距毫无美感。狄拉克在1963年的《科学美国人》写到:“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符合实验结果更重要”。“美感是第一道关卡。丑陋的数学在世界上无法生存”, G.H.哈代则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下了定论。
于是,我们逆向思考一下,对于用户界面之美,我们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方法,用数学来界定美,而非依靠个人灵感驱动美。正如黄金分割可以勾画出漂亮的构图。
人因工程就是与此相关的这样一门学科。人因工程发轫于英国,1947年7月12日,英国海军成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研究组,专门研究如何提高人的工作效率问题,后来的1950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用“Ergonomics”这样一个术语来表达人因工程学。从定义上看,人因工程,就是研究人-机-环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人机界面设计,则是人因工程的重要研究内容,该领域试图用科学化的方法、数量化的方法,指导用户界面设计。
我们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颜色来解释人因工程。人对不同颜色,有不同的认知判断,比如在交通指挥体系当中,红色就代表危险或者告急;黄色代表情况必须要格外注意,绿色代表安全无阻,蓝色代表除了红黄蓝之外的需要额外注意的东西,白色则无特定用意。颜色认知来自我们的基因,有毒的昆虫,身上往往有鲜艳的红色或者黄色,见到这些颜色,我们会本能的躲避或者退让。而不同的颜色,对于计算机来说,都可以还原为一串十六进制,比如代表红色的“#FF0000”。你看,人类的情感认知,和机器能识别的数学符号就这样关联到一起。
正因如此,对于一直在研究用户界面的王成录博士来说,他希望通过人因工程的方法,将美学感受,量化为数学工程。“年轻人和老年人对画面的感知能力就是不同的,年老的人看不了特别晃,变化很剧烈的画面,这和大脑本身机理能力有关,和视网膜感光细胞衰老程度有关;再比如经过华为的研究,欧洲人的视觉和中国人的视觉体系,对于红色的感受也完全不同,在中国非常漂亮的红色,欧洲人看起来就可能很刺眼”,王博士举例,这些信息都能够直接进行量化分析。
王成录博士坚信艺术是最高形式的科学,无形的美学问题,一定可以转化为有形的数学问题。一旦问题界定到数学范畴,华为这样的中国高科技公司也更有用武之处。毕竟,全世界都知道咱们的奥数成绩好,数学可以帮我们用可验证的方式做到“又快又美”。
05
万物时代:是无数个,更是一个
回顾历史之后,接下来不妨就开始预测未来。正如开篇所讲,用户界面的更新,往往伴随着硬件设备形态的更迭。也就是说,不单单是用户界面的变化,也是信息终端本身的演变。如同台式机变成了笔记本,笔记本又变成了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之后,又会是什么?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间接了回答用户界面要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自从苹果发布iPhone之后,业界一直在寻找智能手机之后的下一个计算终端,但是一系列被赋予期望的候选者都折戟沙场,这个名单包括: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汽车、智能电视、智慧屏幕等等。尽管这些终端也赢得了一些用户,在一些场景当中甚至独一无二,比如电视之于客厅,汽车之于驾驶,手表之于心率监测,但是它们都没能完成对智能手机的单一替代。甚至苹果和谷歌两个开创了智能终端市场的公司也没想到新主意。
无论从市场价值看,还是从使用频次来看,智能手机依然是用户当仁不让的王者。以目光所及,似乎短时间内也看不到挑战者。但是,这真的意味着终端换代不会出现么?或许还有第二种答案,那就是终端换代很可能已经到来,但不是一个终端对一个终端的替换,而是很多终端,对单一终端的替换。
这个判断的依据,源自长久以来设备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技术演化历史来看,人和机器的关系中,人一直是主体,设备的进化,就是人机便携性的进化。在PC台式机时代,我们要使用计算机,需走到特定场所,办公桌,书房,这太不方便。于是很快人类就发明了笔记本电脑,可以让我们走到哪,把计算能力带到哪。但是它还是太大了,于是接下来,笔记本电脑变成了尺寸更小的智能手机。
但到了现在的后智能手机时代,尺寸再精巧化这条路已经难以为继。因为再缩小尺寸,设备可用性就会随之下降。乔布斯曾经认为,没人喜欢比4寸屏幕更大的手机,但是他错了,三星、华为等掀起的Note、Mate系列大屏幕手机,成了用户更喜欢的潮流,于是iPhone也有了自己的Max版本。谷歌曾经试图用AR 眼镜,这种小尺寸,大屏幕(虚拟)的方法来取代手机,但受易用性(眩晕感)、安全性(对人的注意力的影响)的制约,后来无疾而终。
可是,如果智能设备不能更小,还如何更便携,多设备替代单一设备,就是另外一种答题思路。既然单一设备无法更便携,何不让处处皆设备?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都有一个计算设备能让我们触手可及。
智能手机时代之后,为何不可是智能万物时代?在智能手机之后,虽然没有一个设备可以向智能手机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计算芯片和连接能力,正在源源不断的内嵌在任何可以通电的设备上。万物互联,万物智能,正在从理想变为现实。
不过看似美好的万物时代,会造成另外难以解决的问题——万物的用户界面问题。
人脑是天生慵懒的,我们的手脚是协调并用的,我们的大脑不喜欢在不同的设备之间,不同的用户界面之间跳来跳去。实际上,正是由于智能手机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在朋友圈、推特、Instagram上秀图片,于是智能手机这样一个单一设备取代了数码相机。如果一万种设备,有一万种界面,对人脑而言是不堪重负的。而如果用一种界面统一所有设备,似乎也不可取,毕竟这些设备的大小、性能,物理特性,几乎毫无关联。
更何况机器讨厌复杂的设计,如果在万物时代,为了让人们在任何场景当中,都能提供恰当的功能,以现在的设计来看,就要实现功能冗余。举个例子,就是智能手机能干的事情,万物都需要能干。智能手机能拍照,智能汽车也要能拍照,智能手机能玩游戏,智能电视也要能玩游戏,智能手机能播放歌曲,智能音箱也要实现音频解码。显然,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方案。
一方面,冗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浪费,另外一方面,复杂设计,会带来机器的可靠性下降问题,和成本上升问题,也无止境的产品售后服务问题。至于用户界面,似乎更加复杂不堪,我们如何在不同屏幕尺寸,不同形态的产品下,保持同样的消费者体验?
在和王成录博士的交流中,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分布式”。何为分布式,就是当用户的设备使用环境,从单一终端升级为多终端,当使用者真实的体验在不同终端面临割裂时,构想一种跨终端协同。在分布式场景下,单一硬件边界被打破,万物为一物的超级终端出现。在这个超级终端上,应用可以像调用一个终端(一物)的系统资源一样,一样调用所有终端(万物)的资源能力,终端之间实现完全的互操作和共享。相比较而言,目前的跨终端协同还仅限于简单的数据传输。
要实现这样的分布式,王博士认为需要三个技术条件:
其一是解耦能力。
分布式平台需要系统做全栈解耦,如果要做比喻,就有点像乐高玩具,不同的模块之间互相独立,根据需要(硬件配置)在进行组合拼装。
正如前言所述,华为已经在内部生产线实现了这种解耦能力,可以用一套代码,支撑生产线上的全系列手机。系统只要知道具体的硬件配置,就可以自动加载需要的模块。
其二是“软总线”能力。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连接计算机内部体系的网络结构。有了总线,计算机的不同元器件,才能协同联动工作。
华为将总线概念,从计算机内部,放大到设备外部,甚至整个智能设备体系之间。按照这套体系,对用户来说,每一个设备,都可当作用户界面的入口,“软总线”或者说虚拟总线,将多设备看作为一个单一设备。换句话说,对“软总线“支撑的用户界面来说,不同的设备,不再是一个个的单一设备,而是可以看作一个虚拟的,宏观设备上的一个功能。
其三是应用迁移能力。
顾名思义,就是解决应用在不同平台迁移的问题,现在常用智能应用几乎都基于手机,如何将这些丰富的应用,以最小的代价延伸万物上,比如车上、音箱上、电视上等等。
但是在这三项技术条件之上,还有最根本的基础软件能力。
过去的十年间,是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十年间,中国的硬件设备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应用场景案例,独步于世界前列。不过王博士感慨,涉及系统级平台开发的基础软件能力,始终是国内软件业一个短板。我们在硬件生产上,有了强大的生产线,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在软件开发上,却没能掌握同等的“生产线”能力。而要实现这种基础能力升级,没有长足的技术积累,没有多年的默默研发,是不可能具备的。
不过机遇也在于此,王博士透露,华为的分布式构想,将通过开源模式运作。一方面,华为希望借此输出成熟的底层能力,让产业链直接受益,另外一方面,好的开源运营,也能推动开发者互惠互利,集思广益,共同提升软件能力。
06
小小世界:浑然一体
最后,如果这样一个分布式构想真正出现,我们的世界会变成怎样?
我们不妨畅想,一个用户,他/她的院子里有无人机,手里有智能手机,客厅里有智能音箱、台灯、电视,那么未来的用户界面,可以将这三个设备视为一个虚拟的“大设备“。用户都能够将音箱的扬声器,作为手机的声音装置,将无人机上的摄像头,作为手机的拍摄装置;反过来亦然,无人机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上的计算能力,进行人脸识别,音箱也可以用电视或者台灯上的传感器,来感知房间环境,调整声音播放模型。如果用云计算的理解来理解,我们大家可以认为这一用户界面下,设备即功能、即服务,Device as a Service。
于是,多智能设备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智能体——超级终端。
这种设想并非曲高和寡,有学者甚至认为地球就是这样一个单一综合体,而非独立的海洋、山脉、沙漠、丛林。20世纪60年代,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洺夫洛克提出了盖亚假说,在这个假说中,洛夫洛克把地球比作一个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但这并不代表世界是有生命的,而是说明生命体与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海洋、极地冰盖以及我们脚下的岩石——之间存在着复杂连贯的相互作用。
既然,无机物占据主体的地球,都可视为一个有机合体个体,确实存在智能因素的万物,有何不可设想为单一综合智能体?
至于用户界面问题,将由AI算法将帮我们解决。此时万物系统不同终端的用户界面,将基于人因工程方法,由AI,智能化的匹配设备硬件特性和使用场景,实现千人千机千面。正如生产线上的硬件系统配置,已在通过AI算法,根据硬件规格,自动被推送那样。
从后端终端生产配置,到前端用户界面使用,全面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
其实万物时代畅想的背后,是更基础的技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交叉融合。
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生存以来,一直有两种数字化技术伴随左右,一种是信息技术,代表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一种是通信技术,代表传输信息和数据的能力,信息技术的阶段性技术顶点是深度学习为代表的AI技术,通信技术的阶段性技术顶点,是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两种技术互不越界。但是在万物时代,这两种能力则会相互靠近,难以分离。
我们设想,万物可以虚拟合为一物,但没有5G连接技术,这个互联互通就无从谈起。我们继续设想,千人千机千面,用户界面会根据人-机-环境三要素“,基于人因工程,自动匹配软件特征。没有AI,我们也无法将万物整合的“一物”,用更个性化的方式(千面)提供给用户使用。
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机器已经是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一员,我们大家可以同意乔布斯的判断,用户界面的重要程度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Netflix有部关于工业设计的纪录片,叫《抽象:设计的艺术》。其中关于数字产品设计一集,故事主角是伊恩·斯波特,知名设计师,他此前主导了Instagram的视觉设计。伊恩斯·波特在片中感慨:人类体验宇宙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视觉,通过随身携带的这个设备(智能手机),就能让你及时捕捉你所看到的,然后把它发送到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这又仿佛把你本人传送到了远方,这是前所未有的将远距离的事物拉近的方式。
所以你看,用户界面还是你感受世界的方式。
在后智能手机时代,在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时代,万事万物本身之间的距离也被连接技术拉近了,它们成了某种浑然一体的东西。或者我们大家都认为它们在拉近世界,让我们更好的感知、认知世界,或者它们更进一步变成了世界本身。
在全球每一个迪士尼乐园,都放着一首歌,叫《小小世界》,主旋律歌词是一句:This i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在其中一个翻译版本中,歌词是这样翻译的:
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欢乐与悲伤
大家互相帮助 心连心 组成了这个温暖的小世界
在这个小小世界里不分你我
在任何地方只要微笑就能成为好伙伴
大家手牵手 围成圈 组成世界大家庭
在这个小小世界里不分你我
万物时代,一花一世界。人机用户界面,就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与世界对话的舞台。十五年技术换代周期临近,Technology should be for social good,新技术愿景也应如此美好。
编 辑:章芳
 于十城相见,品极致豪华 一汽红旗E-HS9为您描绘中式高端画卷
于十城相见,品极致豪华 一汽红旗E-HS9为您描绘中式高端画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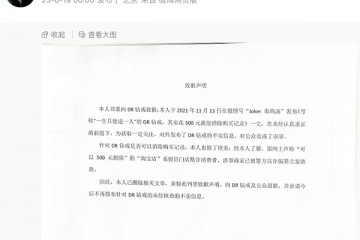 “DR购买记录可删”被证实是谣言,传谣者公开道歉
“DR购买记录可删”被证实是谣言,传谣者公开道歉 电源也需“三防”,铂陆帝首款户外三防户外电源AC60评测
电源也需“三防”,铂陆帝首款户外三防户外电源AC60评测 VMware Explore 2022 China,赋能中国企业加速实现云智能
VMware Explore 2022 China,赋能中国企业加速实现云智能 5G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上起到很多作用 高通孟樸:多方协作必不可少
5G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上起到很多作用 高通孟樸:多方协作必不可少 进博会ESG声音:外资企业融入双循环 高通以ESG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博会ESG声音:外资企业融入双循环 高通以ESG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通首席商务官吉姆·凯西2022进博会分享:加速汽车领域数字化转型,与
高通首席商务官吉姆·凯西2022进博会分享:加速汽车领域数字化转型,与 高通孟樸:与中国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工业互联“智造”未来
高通孟樸:与中国产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探索工业互联“智造”未来